《可憐的東西》艾瑪史東獻祭級表演、科幻電影的寓言寄情與祝福|影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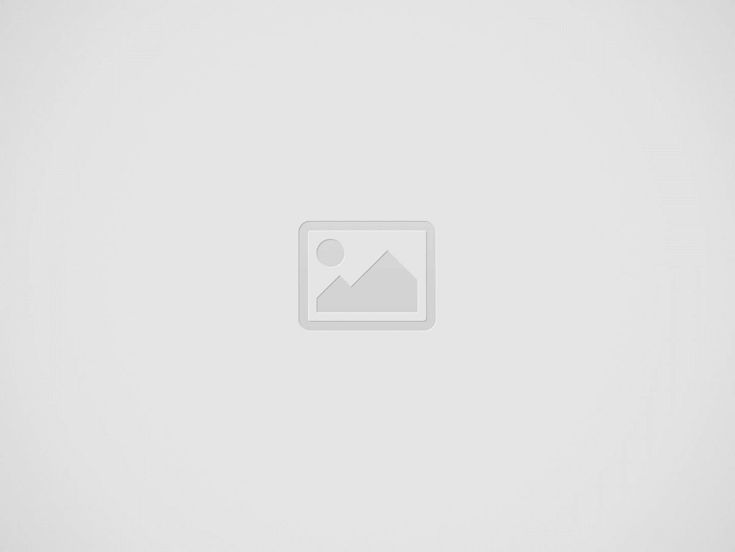

艾瑪史東再度問鼎奧斯卡影后電影《可憐的東西》延續了希臘名導尤格藍西莫的怪誕敘事風格,煥然了影迷觀影樂趣,也絕對是艾瑪史東與導演職涯中,最有趣的喜劇作品、也最有勇氣的一次挑戰與嘗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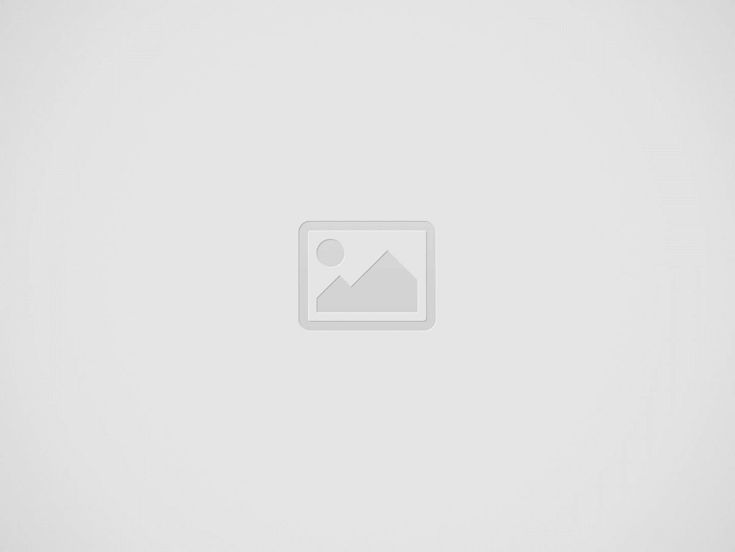

《可憐的東西》改編自阿拉斯代爾格雷的同名書籍之作,講的是瘋狂科學家打造出「女科學怪人貝拉」並從她腦齡〇歲開始教起。在威廉·達佛所飾演的哥德溫博士「上帝」養育與觀察之下,貝拉得到了讓身心靈完全自由的發展空間,因為她的一切變化對於博士而言都是珍貴的實驗紀錄。尤格藍西莫導演對於「政治正確」性別意識有著高度敏感自覺,且不只如此,導演也成功地把議題轉化為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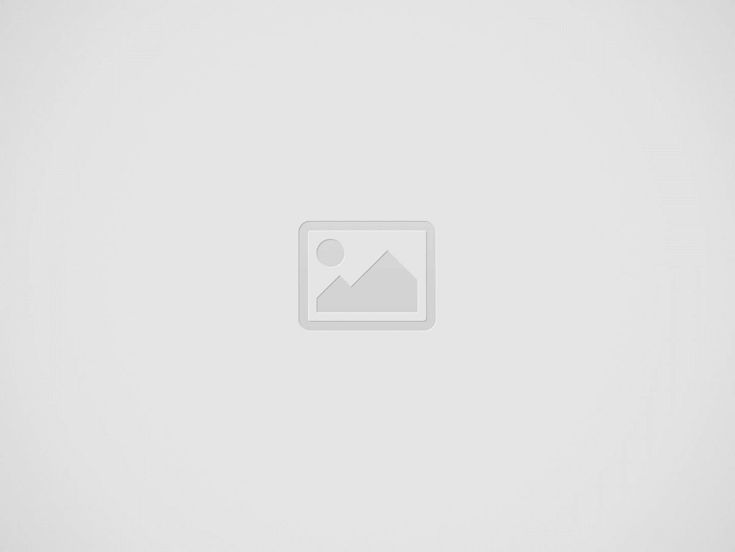

《可憐的東西》是很服務影迷導向的一部電影。尤其片頭黑白畫面、加上片中佈滿著扭曲線條、詭譎氛圍,甚至帶有點恐怖片況味的氛圍營造,是直接帶領著觀眾搭上電影史的時光機、一口氣回到一百年前 1920 年代表現主義電影的盛世,直接與經典之作《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產生連結。說是尤格藍西莫在致敬也好,然而電影中所描述的歌德糜爛腐朽氣息,恰恰也是原著中維多利亞時代的末期輓歌。濃郁形式也讓《可憐的東西》成了尤格藍西莫至今作者風格美學最為強烈的作品之一,且是形隨機能的一種極端之必須。
不可諱言,性別議題電影發展至今,處處碰壁,變成了 Poor Things。或許大家會說《神力女超人》和《芭比》很賣座啊?是啊。但事實上是:獲獎無數的《神力女超人》卻在奧斯卡獎上〇入圍;後來《芭比》有入圍奧斯卡獎了啊?偏偏女主角瑪格羅比和女導演葛莉塔·潔薇還是神奇地被排拒之於入圍名單之外。世上多的是賣座又拿獎的雙贏電影作品,但這對女性電影而言那是很困難的事。要不是《可憐的東西》異常華麗地「出怪招」,是要怎麼贏牌?
用視覺美學衝擊觀眾到最大還不夠,艾瑪史東也蹽落去:貝拉從牙牙學語的嬰兒腦開始發展,卻是擁有著會分泌賀爾蒙的成熟女體,很快地嚐到滿足性慾所帶給自己的快樂並食髓知味、樂於天天愛愛。智力尚且還在成長且沒有受到人世間道德教育禁錮的貝拉,便出現了思想極度純真、行為極度淫蕩的高反差人格,而舞台劇語言的違和感既帶著宣言式性權發表、也是表現演技的極致衝撞。艾瑪史東全片數不清的性愛與裸露戲、置肉體於度外,卻又在精神向度上做出鏗鏘與純粹的表達,儼然是獻祭級的表演。
科幻電影太適合寓言與寄情。
歷史上思想革命在發起時被社會不待見、多年百年過後才被社會理解與接受的案例太多。
讓子彈飛的時間不知道要等多久?等待的這段年歲,就讓科幻電影借古喻今一下亦無不可。
很多影迷很喜把《可憐的東西》譽為「《芭比》的進階版」、「超越《芭比》」、「更高明的《芭比》」或「更好看的《芭比》」…… 果然把故事背景時代「往前挪一兩個世紀」,諷喻父權起來就沒有那麼傷害當代男人自尊了。
我對於喜愛《可憐的東西》的生理男性觀眾其實是非常敬佩也充滿祝福的,他們有著被挑戰的勇氣與樂見時代進步的覺醒潛力。至於尤其對於坐擁高社經位階甚至滿腹文化的生理男而言,若不喜歡《可憐的東西》其實沒有關係的,你最優雅的應對表現其實就是別出惡言。套句朱家安老師的話:這麼有文化資本,怎麼會連有禮貌一點的評論都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