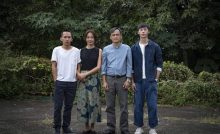《無聲》金馬入圍8項大獎看點┃電影專題┃影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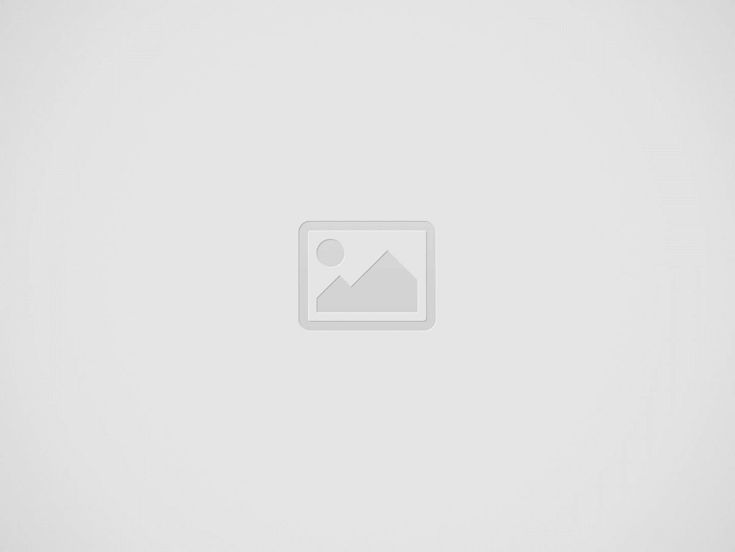

甫上映就取得票房與討論度的國片《無聲》參考自台灣真實發生的校園事件,入圍2020年第57屆金馬獎的成績僅次於入圍11項的《消失的情人節》與入圍9項的《同學麥娜絲》,究竟為何這部電影會是台灣人年度必看佳作?入圍獎項名稱就是看點,一起來一探究竟。
最佳新導演
曾以短片《無名馬》入圍金馬獎、又以植劇場《天黑請閉眼》在金鐘獎斬獲佳績的導演柯貞年,長年關注與思考霸凌和性侵議題,拍出《無聲》如此理所當然。電影聚焦於聾人無法融入聽人世界而在校園內發展出一套彼此取暖的生態系,然而孩子團體中的惡質事件卻是始發於糟糕的大人!這份以鞭得小力代替大聲疾呼控訴,既有著柯貞年導演身為大人本身的自省意味,更絕妙的是《無聲》其敘事形式呼應了聾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身為導演的柯貞年並沒有放棄從這群孩子的視角出發,同理與挖掘出他們的美好心靈、並期望世界透過《無聲》這一扇窗能更理解這群孩子的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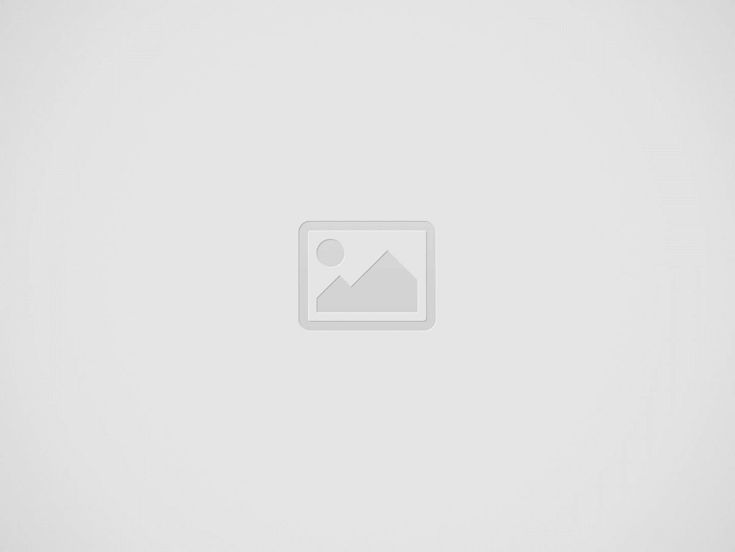

最佳男配角
史上首位入圍金馬獎的韓國演員金玄彬,在《無聲》中飾演校園老大「小光」。小光是學校裡第一個向男主角張誠釋出善意的人,他在扮裝舞會上打招呼並問張誠「新來的?」積極向他示好、摸了張誠的手,要他動/跳舞/玩起來。那時穿著黑西裝的小光看來非常無害。但在同一場舞池戲的最後一顆鏡頭裡,小光成了張誠的背後靈,像一抹黑影那般地附著在張誠的身後、隨之跳動,不分你我。其實電影在金玄彬的第一場戲就預告了他對劉子銓所飾演的張誠的人生所將造成的「陰影」,你發現了嗎?
最佳音效、最佳原創電影音樂
既然是講聾人的故事,《無聲》的聲音工程就不能馬虎。盧律銘的音樂陪伴了每個主要角色的心靈轉變和震撼的瞬間,把鼓聲、拍手聲、呵氣聲和氣若游絲的吟唱都化作為這些聾人或可理解也曾感受過的震動與波形,疏落有致又不致搶戲地襯疊成他們的情緒靈體;郭禮杞與李東煥更強化了每個聾人在打手語的情緒表達時空氣的流動、呼吸強弱轉換時的氣勢較勁,以及聾人和聽人間溝通之際的聲音情境。
於是觀眾不是聽覺突然變得靈敏了,而是感受度驟然被提升了——電影語言裡難的其實從來就不是看得見且早已有跡可循的影像語言審美系統復刻追隨(即便連這部分柯貞年導演也做得頗為高分),而是看不見卻能震撼心靈、詭譎得又像是無字天書一樣存在的聲音語言營造能耐。《無聲》講的是聾人的身心靈體感世界,開的卻是聽人的天耳、以及連聽人都承受不起的世界真相,這不是挺諷刺的嗎?尤其當電影都拍得若此擲地有聲了,明明是該看得懂電影的聽人們,卻反而想要裝聾了。
最佳新演員
陳姸霏在《無聲》中飾演一位佛系受害者「貝貝」。身為校園中檯面上和檯面下主動或被迫「一起玩」的最底層階級成員之一,貝貝活得卻跟救世主一樣,活到讓歐美觀眾無法相信「世間怎可能存在有這種女性?」但這不正正就是父權亞洲對女生所設下的道德與個性高標?只是這般大家早已適應得很習慣、視為理所當然的「好女孩範本」一旦真的存在了,大家反而又不相信真的會有這樣的人了。
最佳美術設計
作為一部特異的校園電影,《無聲》既寫實又魔幻。舉凡一開始的校園舞會,宿舍房間,到霸凌的廁所、性侵的體育室,乃至於廊道間的八仙和游泳池畫作,處處校園感洋溢但這般「深山裡的校園意象」,既有著一群孩子被拋棄、被藏匿、被密室,甚至是內部情事無法被揭露的複合無助感,更適度讓觀眾感受到「紅林」是一所架空的校園,這樣一來便讓人無法清楚去對位故事究竟來自南聰、苗栗、或花蓮?這從任何角度來看都不啻是種自外於「真實校園性侵事件」鏗鏘的保護色。若問《無聲》的美術為何之所以要做得讓人有感?我會說連這都是一份製片過程中就已經考量過,不想讓真實世界裡的任何人被對位、被為難的溫柔使然。
最佳剪輯
為闡述不同立場之人的各種不同生命困境,《無聲》以非單一角色觀點講故事,行影期間必然會有視角的轉換過程,且不只兩位,而是至少三位以上在看這整起事件。這對於時間篇幅有限的電影敘事而言是種風險。然而在觀賞《無聲》時觀眾並不會感覺到有角色視角的跳躍,反而有種陷入與爬出困境後又立馬跌入另一人為陷阱的無力與無奈,難的就是這一份立場不同又環環相扣的受害者接力賽中無人能贏。電影要把這麼剪不斷理還亂的共犯結構爬梳出個所以然,甚至做到讓觀眾能夠一目瞭然的剪接鋪排,除了關懷,還必須冷眼才能辦到。
最佳原著劇本
《無聲》發想自真實校園性侵事件,電影推出後成功引發社會關注、卻也陷入《沉默》作者陳昭如是否該被致謝甚或電影該否擁有版權的爭議之中,儼然台灣年度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最佳電影。事實上翻拍自社會真實事件的劇情電影通常都有改編成分,然在電影獎項上一旦入圍,只要不是改編自小說散文甚或詩集就仍屬「原著劇本」而非「改編劇本」獎項範疇。以2012年第49屆金馬獎入圍名單為例:入圍最佳原著劇本的《浮城謎事》故事來自於網路「看我如何收拾賤男與小三」之貼文,該故事號稱來自於真實經歷;同屆鮑鯨鯨則憑自己原著《失戀33天》改編的電影劇本得到最佳改編劇本獎。
《無聲》的原罪來自於這個故事太過獵奇、活像小說。但故事的前身卻是來自於各方真實案件的集成,儼然N個《浮城謎事》。打定要碰觸與翻拍這些比小說更震撼世人的真實故事群或許才是《無聲》注定惹出爭議之處,不論田調方式為何,最終指向的事實本就會與《沉默》內容重疊。想拍性侵題材出自於導演創作慾望,但怎麼就被說妳因此涉及處於「不禮貌的改編」的風險之中?就像想打扮漂亮出自於女為己悅而容,但會被說妳因此暴露在「受到性暴力」的風險之中。難怪我看《無聲》時覺得貝貝一定也有這樣的感觸:性侵這種事就是,明明不是妳的問題。最後都會變成是妳的問題。
《無聲》是2020年最重要的台灣電影之一,沒有入圍年度金馬獎最佳影片已足以讓筆者為窈七不平。至於最佳原著劇本獎?就看決選評審要當田季安還是磨鏡少年了。
本文獨家授權